□ 法律文化
□ 殷啸虎 (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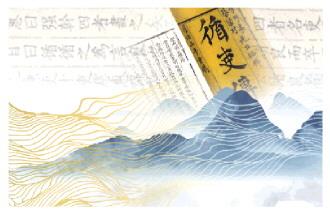
“循吏”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,主要是指那些奉公守法、清正廉明、推行教化的地方官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对循吏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义,即“奉法循理之吏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沿袭了《史记》的体例,作《循吏传》,从此循吏便成为那些清官良吏的专有名词。由于循吏是相对于“酷吏”而言的一个概念,酷吏是指那些奉行严刑峻法,“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”的官吏,因此,后世也将奉行刑罚和主张教化作为两者区分的标准。其实,循吏虽然主张教化,但同样非常重视法制的作用;特别是汉代在制度上“汉承秦制”,主张“以吏为师”的同时,融礼仪道德教化于依法治理,因此,循吏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法律观,也成为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汉代的循吏作为“吏”,其基本职责就是贯彻执行朝廷的法令,维护地方秩序。他们虽然不像酷吏那样“专任刑罚”,但都要“奉三尺律令以从事”。所不同的是,循吏在治理实践中,更注重教化的作用,“以化治称”。而法律则是作为推行教化、实现治理的重要手段,这也是汉代循吏法律观的核心要义所在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,就是董仲舒和黄霸。
董仲舒是《汉书·循吏传》中第一个被提到、却又没有列入《循吏传》的人。他虽然主张“任德教而不任刑”,认为“刑者不可任以治世”,但同时又强调“正法度之宜”,把法律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,这就是著名的“德主刑辅”的主张。因此,董仲舒可以说是奠定了循吏法律观的理论基础。
而黄霸则堪称是循吏法律观的实践典范。他虽然是“入财为官”,即花钱买的一个小吏,但“以廉称”,而且“为人明察内敏,又习文法,然温良有让,足知,善御众”。汉宣帝“闻(黄)霸持法平,召以为廷尉正,数决疑狱,庭中称平”。后出任颍川太守,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,“治为天下第一”,“自汉兴,言治民吏,以(黄)霸为首”。
从汉代循吏的从政和治理实践来看,他们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:
其一,注重依法治理,维护地方秩序。循吏虽然不同于酷吏的专任刑罚,但在治理实践中同样非常注重依法治理。如前所述,循吏是“奉法循理之吏”,“奉法”是前提。地方官的基本职责就是执行朝廷的立法,维持地方秩序。一些循吏本身就是精通法律的人,如黄霸“少学律令,喜为吏”;东汉时的循吏王涣也是“读律令”。他们在地方治理的实践中,注重运用法律手段。王涣任温县县令时,“县多奸猾,积为人患。(王)涣以方略讨击,悉诛之。境内清夷,商人露宿于道”。东汉另一位循吏刘宠任会稽太守时,也是“简除烦苛,禁察非法,郡中大化”。此外,他们也很注重治理人才尤其是法律人才的培养。西汉著名循吏文翁任蜀郡太守时,就曾选派郡县小吏去京城长安,“受业博士,或学律令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“政平讼理”也成为循吏的一个重要标准。
其二,主张德主刑辅,强调教化为先。如上说言,循吏是“奉法循理之吏”,“奉法”是前提,“循理”则是循吏的特点。他们不像酷吏那样机械地照搬法条,而是从情理出发,根据具体情况,灵活适用法律。而“循理”的主要依据,就是儒家的经书。他们将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作为治理的主要手段,这也是与酷吏的主要区别所在。汉代的循吏基本上都是熟读经书,在治理实践中也是以儒教主张的礼仪道德来教化百姓。《汉书·循吏传》开篇在谈到董仲舒等人时,就称他们“通于世务,明习文法,以经术润饰吏事”。黄霸曾师从著名大儒伏生学习《尚书》,“力行教化而后诛罚”;东汉秦彭任山阳太守时,也是“以礼训人,不任刑罚”。他们在司法实践中,也往往通过教化去化解矛盾,解决纷争。东汉许荆为桂阳太守时,有兄弟为争财而打起了官司,许荆认为“教化不行,咎在太守”,请求朝廷对自己问责,结果兄弟俩悔恨交加,“各求受罪”。东汉仇览任亭长时,有母亲告儿子陈元不孝,仇览认为这是自己“教化未及至耳”,亲赴陈元家进行劝导,结果母子相拥而泣,陈元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孝子。时任考城县令的著名循吏王涣听说仇览能“以德化人”后,专门请他担任主簿。东汉刘矩任雍丘县令时,“民有争讼,(刘)矩常引之于前,提耳训告,以为忿恚可忍,县官不可入,使归更寻思。讼者感之,辄各罢去”。
其三,奉行用法宽平,倡导宽猛相济。循吏虽然也主张依法治理,但他们奉行用法持平,倡导宽猛相济,这是他们与酷吏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之处,也是“奉法循理”两者结合的具体体现。同董仲舒一样,在《汉书·循吏传》开篇被提到、但没有写进《循吏传》的儿宽(又作倪宽),治民奉行“缓刑罚,理狱讼,卑体下士,务在于得人心”;黄霸也是“处议当于法,合人心”,在他的治下,“狱或八年亡(无)重罪囚,吏民乡(向)于教化”;东汉的王涣虽然“政尚严猛”,但也“以平正居身,得宽猛之宜”而著称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开篇中,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:“法令所以导民也,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,良民惧然身修者,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,亦可以为治,何必威严哉?”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揭示了循吏法律观及其实践的基本特点。汉代的循吏将先秦法家主张的法治与儒家主张的礼治融于治理实践,促进了礼法结合的进一步发展,对中国古代以“德主刑辅”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